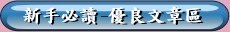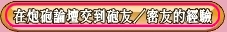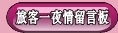被誤會的女性
在台灣常常將與外國男性交往的女生冠上:「外餐妹」或是 CCR (Cross Cultural Romance)的稱號,選擇伴侶的時候,彼此的性別、文化、種族、年齡...等,為什麼會被社會輿論加以評論呢?到底與外國人交往,有什麼問題呢?一、道德恐慌與俗世惡魔
土耳其男子王凱傑與台灣女人發生性關係的影片外流,還自爆與上百名台灣女人上過床,造成台灣社會一片騷動。新聞上面指出,影片中的台灣女人積極主動地與王凱傑發生性關係。輿論分兩派,一派大力抨擊王凱傑,將他描繪成一個外來的入侵體,是個不負責任的浪子,玩弄台灣女性的混蛋。另一派則將道德的帽子扣在台灣女人身上,認為這群女人崇洋媚外,不知檢點,因此「活該被玩弄」。
隨後,一則新聞再度引發台灣社會道德恐慌。一名台灣女子在捷運上,穿著短裙,公開坐在白人男友的大腿上。有人用手機拍下影片上傳到網路上。輿論批評的居然不是這個擅自拍下影片又沾沾自喜上傳到網路上的無聊之士,而是坐在白人男性大腿上的女子,說她有礙風化,在房間裡面崇洋媚外就算了,還將性事帶到公共場域來。
《百吻巴黎》作者楊雅晴在新聞上暢談自己於法國索吻的經驗,不令人意外地引起台灣男性網友的全面抨擊,依舊跳針地說楊雅晴崇洋媚外,說楊雅晴「有辱國格」,還說她為什麼偏要「百吻巴黎」,而不「百吻菲律賓」。
知名的社會學家史丹利˙柯恩(Stanley Cohen)在其經典著作《俗世惡魔與道德恐慌》(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中指出[1],我們社會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出現一陣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之下,一個特定的群體會因為威脅到主流價值觀與既有秩序,而引發社會中的一波道德恐慌。也就是說,道德恐慌與特定的時空與文化背景有關,也會隨著時空背景的遷移而有所轉化與變形。
這樣的道德恐慌與主流媒體有很大的關係。主流媒體將對常規社會具有威脅性的群體建構為某種「俗世惡魔」(folk devils),引起主流社會的道德恐慌。但有趣的是,這樣的媒體建構與渲染,居然也會反過來加強「俗世惡魔」的叛逆。也因此,媒體與叛逆、道德恐慌與俗世惡魔之間,反而存在一種微妙的共生關係。
柯恩的研究主要關注的其實是六〇年代英國社會各種青少年叛逆文化,包括摩斯族(Mods),泰迪男孩(Teddy boys)與光頭黨(skinheads)。有趣的是,柯恩關注的大多是「陽性」的俗世惡魔。在後女性主義的年代,隨著陰性威脅與女性情慾的崛起,也有越來越多「陰性」的俗世惡魔誕生。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越來越多西方男人前往亞洲國家旅行,也越來越多亞洲女子前往西方國家遊歷,異國戀情與情慾流動因此大量產生,造成亞洲社會新一波的道德恐慌。這些不顧常規社會規訓,主動追求西方男人的台灣女子,很快地在媒體渲染與網路輿論的雙重建構之下,成為台灣社會新興的「俗世惡魔」。這些陰性的俗世惡魔到底對台灣常規社會造成了什麼威脅?
二、閹割焦慮、殖民情結與厭女心態的混合體
這群與西方男性交往的台灣女子作為新一波的「俗世惡魔」,真正威脅到的正是台灣父權社會。這群「俗世惡魔」之所以成為社會集體獵巫的對象,是因為她們不只衝撞了父權社會規訓女體的框架,更精確地踩到了台灣男性閹割焦慮、殖民情結與厭女心態交混的大地雷。
上述三則新聞雖然都是同一波道德恐慌下的產物,卻各自代表了三種不同的陰性威脅。王凱傑事件代表的是家居空間的陰性威脅,這個新聞事件之所以可以引發看似對立的兩種輿論,就在於家居空間的陰性威脅沒有被看見。除了辦案的警察之外,沒有任何人真正目睹了這些神祕的性愛影片。因此,一派輿論可以無視女性的自主情慾,基於女性作為被動(害)客體的立場,譴責「壞男人」王凱傑,扮演父權保護者的角色。另一派則一律譴責所有「越界」的「壞女人」。不管是譴責還是試圖「救贖」這些「墮落女子」,事實上都是源自同一套父權體系的思想。輿論兩派看似對立,實為一體。
相較於王凱傑事件,捷運坐大腿事件卻沒有任何一個人譴責白人男性,一面倒地抨擊影片中的台灣女子。這位台灣女子穿著暴露身體的短裙,首先挑戰了父權社會對女體的規訓。更重要的是,這名女性在「公共空間」也展露了自己的自主情慾,引發的是台灣常規社會一直以來存在的「公共性恐慌」。而這樣的公共性恐慌一旦與對西方男子的焦慮結合,就成為新一波的道德恐慌。於是,這一波道德恐慌背後隱含著非常複雜的因素,是厭女情結、公共性恐慌,以及面對西方他者的閹割焦慮之混合體。
最後,楊雅晴的「百吻巴黎」,則代表了完全逃逸於台灣父權社會掌控之外的自由女體。楊雅晴代表的是新一波當代少女離開國家,積極在世界各地旅行的自由。這樣的自由看在台灣男人眼裡,居然成為一種「叛國」的慾望。這時台灣成為「家居空間」,而西方國家則成為「家庭以外」的「野生空間」。脫離了家/國父權社會規訓、在家/國以外的野生空間進行自由冒險的女體,因此被譴責、被妖魔化,也被扣上了「有辱國格」這頂父權之帽。
不管是家居空間的陰性威脅,公共空間的情慾展示,還是逃逸於家/國規訓體系以外的自由女體,這一波波新聞背後一方面反映出當代少女的自主情慾與身體自由,一方面也顯示出台灣男人的閹割焦慮與殖民情結。面對西方男人,台灣男性總是先把對方想像成一個更為強大的「他者」。從台灣男性普遍對西方男性生殖器長度的扭曲刻劃,我們就可以輕易看出台灣男人的閹割焦慮。
台灣男人的閹割焦慮與殖民情結緊緊相扣。網路上流傳著一種說法:「台灣女人就是好高騖遠,喜歡跟高人一等的西方男人交往。」這樣的言論基本上反映出台灣男人從殖民情結而來的身份焦慮。事實上,正是這些台灣男人將西方人想像成「高人一等」的他者。 當與西方男人交往的台灣女人與對方分手或離婚時,台灣男人往往會冷嘲熱諷地表示「與西方男人交往就是會有這種下場。」這樣的說法除了把女性塑造成情慾關係與婚姻中的被動客體(彷彿台灣女人不可能主動要求離婚,不可能自己想分手) 之外,背後反映出的仍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殖民思維,認為台灣女人想要跟「比較高等」的男人交往,因此「失敗」了終究只是「活該」。真正加深了殖民意識型態的不是台灣女人,而是這群台灣男人。
但是,這樣的閹割焦慮與殖民情結最後發洩的出口居然不是那些已被想像成「強大他者」的西方男性,而是台灣女性,原因就在於台灣女性的自主情慾。這就是新一波跨國戀情與前一波東西羅曼史不同之處,當前一波東西羅曼史的想像仍停留在非常落伍的「蝴蝶夫人式」刻板印象之中,新一波跨國戀情之所以可以引發道德恐慌,就在於這群台灣女人早已擺脫了父權家/國規訓框架,在遇上西方男人時化身慾望主體,而不是那個軟弱無助、隨時等待被拋棄、甚至願意為西方男性自殺的蝴蝶夫人。蝴蝶夫人尚可被東方父權社會原諒,尚可被「救贖」,因為她是一個被動的受害客體。現代台灣女性非但不是蝴蝶夫人,更是花邊教主、慾望少女,以及那一個個威脅著父權社會框架的俗世惡魔。
三、當台灣男人遇上西方女人
那麼,當台灣男人遇上西方女人呢?網路上總不乏有台灣男人沾沾自喜地表示自己曾與多名「金絲貓」交往,而下面引發的是男性網友的讚嘆而非批評。有趣的是,這時,這些台灣男人居然被視為英雄,而非引發道德恐慌的俗世惡魔。這顯示出新一波的道德恐慌,的的確確與台灣的父權社會體系緊密相連。這不只是文化與族裔的問題,這是性別的問題。
將西方女性不分國籍一律比做「金絲貓」,就像台灣男人不顧王凱傑來自土耳其,基本上也不算太「白人」、太「西方」一樣,是對外來他者的無知分類方式。不過,將西方女性比做「金絲貓」,則是意圖以父權社會意識型態去抵銷自身殖民情結與閹割焦慮的策略。「金絲貓」也好,「黑絲」的也罷,西方女性仍然被視為一個具有優勢的族裔他者。而這時,台灣男性必須透過性別上的「雄性優勢」,去征服這個原先具有「族裔優勢」的陰性他者。也就是說,不管是批評與西方男人交往的台灣女人,還是得意於自己「征服」了西方女人,背後隱含的都是同一套殖民情結與厭女心態。真正鞏固既有族裔位階與性別層級的,就是這群台灣男人。
最有趣的新聞事件要數吳憶樺事件。這一波道德恐慌漫燒到混血兒身上。凡是帶有「西方」(不管是否為白人)血統的,往往會被台灣男性視為具有優勢地位的外來他者。台巴混血兒吳憶樺前陣子回台灣,在西門町一家餐廳與台灣女子熱吻的事件,再度造成社會轟動。不管是吳憶樺的「巴西」還是王凱傑的「土耳其」,都在這一波的道德恐慌中被統統歸類為一個籠統的「優勢西方」。而帶有巴西血統的吳憶樺,因此被視為一個具有威脅性的雄性外來他者。不過,一如往常,台灣男人的抨擊全都聚焦於台灣女人身上,說台灣女人就是崇洋媚外(也不管「巴西」可不可以被歸類為「洋」),說台灣女人就是好高騖遠
但是,這時有網友出來表示,吳憶樺的父親是台灣人,母親是巴西人。於是,吳爸瞬間成為了平復台灣男性閹割焦慮的本土正港英雄,而吳媽則是那個懂得欣賞台灣男人雄性特質、願意「拜倒」在台灣男人之下的西方「好」女人。父權社會的雙重標準與意識型態,在吳憶樺事件中,輕而易舉地被揭露出來。
四、異國戀也有真愛:偏差的層級與主流意識型態的權力掌控
這時可能有人會跳出來表示:「異國戀也有真愛,不是每對異國戀都只要性愛。」然後表示自己非常接受異國戀情,只要對方有「真愛」。表面上,這樣的說法在替異國戀情辯護,批判新一波道德恐慌。事實上,這樣的說法與背後隱藏的意識型態,正是這波道德恐慌能夠被推動的原因之一。
這樣的說法背後運作的,其實是「偏差層級」的建立與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力掌控技術。它先是把異國戀分成兩種,在真愛與性愛之間建立起(根本不存在的)二元對立,接著進行更進一步的偏差排擠與權力運作,將「只要性愛」的西方男人與台灣女人視為「真正的偏差」,排擠到邊緣。也就是說,透過「真愛論」,這種主流意識型態一方面收編了「乾淨」的異國戀,將主流異國戀「去性化」,或是將他們的性愛「乾淨化」,因為這樣的性在父權家庭體系下是可以進行常規生產的「正常的性」,另一方面則將那些在家庭體系「之外」的性建構成「偏差的性」,一口氣排擠到社會的最邊緣。
也因此,「異國戀也有真愛」這樣的說法,非但沒有挑戰到主流價值觀,反而鞏固了異性戀家庭體制結構。從文章一開始提到的三個新聞事件來看,只有楊雅晴最後走入「正常」關係的異國戀,可能受到擁護。與王凱傑發生性關係,追求情慾快感的台灣女性,則會被視為家居空間中偏差的性。而在捷運上不顧公共空間對性與女體的規訓,仍然堅持要展露身體並享有調情自由的那名女子,則因為造成了「公共性恐慌」,而成為最「偏差」的俗世惡魔。
在這樣的層級結構與權力掌控之下,俗世惡魔也被建構出「偏差等級」。在俗世惡魔之外,永遠都有「更偏差」的惡魔,逃逸於主流體系之外。而這個將俗世惡魔頻繁收編與排斥的過程,反映出的正是當下台灣社會運作的一套鞏固主流父權家庭意識型態的權力體系。
五、隨之獵巫的台灣女人
這波道德恐慌總讓我想起歐洲十六、十七世紀興起的獵巫熱。早在1995年,女性歷史學者安˙巴斯托(Anne Barstow)就點出過去研究獵巫熱的男性學者往往因為男性意識型態而忽略了獵巫熱中非常明顯的因素:性別。更精確來說,是厭女情結。[2] 對巴斯托來說,獵巫熱是西方父權社會轉型的關鍵。獵巫熱對女巫進行的種種身體搜查(尋找女性身體上「撒旦記號」的刺女巫者)與折磨(帕本海莫一家,只有母親安娜必須忍受乳頭被當眾切除的殘酷折磨),最後演變成一套規訓女性身體最有效的監控系統。而女人也從中世紀文學中像巴斯夫人(the Wife of Bath)那樣充滿情慾的角色,慢慢轉變成為維多利亞時期典型的「家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
但是,獵巫熱之所以能夠如此成功地發展成規訓女性的父權體系,事實上也與女性自己的參與有關。是的,正是因為女人也隨著男人獵巫,獵巫才會發展成如此有效的監控系統。巴斯托指出,獵巫熱最後引發的是女人對自我的監控。女人看著一個個女巫被公開折磨致死,開始擔心自己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女巫,急欲撇清與女巫之間的關係。到最後,厭惡自己的身體,厭惡自己的陰性特質,厭惡自己是女人。(女孩,請愛自己:Be proud to be a Woman,我的身體我做主)
台灣社會新一波的道德恐慌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獵巫熱到底有什麼關係?關鍵就在於父權社會監控體系的建立。對與西方男人交往的女人做出嚴厲指控的,除了台灣男人之外,也有一群隨之起舞的台灣女人。這群女人一方面拾起手邊的石頭,往俗世惡魔身上扔過去,一方面則急於撇清:「我不是那種女人哦。我不崇洋媚外。」
透過這樣的標籤轉移過程,這群台灣女人沒有意識到自己在鞏固一套終究會反噬自身的父權社會規訓體系。當女巫被獵殺,若另外一群女人不是站出來挑戰獵巫熱背後的厭女情結與父權體系,而是在譴責女巫以及互相糾舉的過程中以求自保,也只會使得獵巫熱演變成一種更具正當性的監控系統罷了。強調我不是女巫,我不是惡魔,最後只是讓女巫獵人更理直氣壯地將女巫綁在柱子上焚燒 。更重要的是,你不知道自己何時也會被綁在這根柱子上,被父權社會審判。
同樣的,在新一波的道德恐慌中,與西方男人交往的台灣女人成為衝撞父權社會框架的俗世惡魔。台灣女人要做的,不是拿起手邊的石頭砸向這群俗世惡魔,而應該與俗世惡魔聯手挑戰父權社會的規訓體系。俗世惡魔終究是女人的盟友,不是敵人。
六、台灣女孩很好上?全球厭女情結與古老的父權迷思
那麼,西方男人就沒有其意識型態問題了嗎?大家都聽過一則說法吧。你在Google上輸入「台灣女孩」(Taiwanese girls),後面會出現「很好上」(are easy)。這時,台灣女孩大多氣憤地表示自己「沒有那麼隨便」,卻沒有意識到這樣的說法本身即服膺了父權社會意識型態。為什麼沒有人說西方男人很好上呢?
女人「隨便」與「不隨便」,「好上」或「不好上」,背後隱含的仍然是父權社會中對女性貞潔的迷思。彷彿女人只能有兩種,前者隨便好上,因此是蕩婦;後者不隨便,會抵抗,因此是聖女。這樣的蕩婦/聖女二元論(whore/ virgin dualism)依舊存在於父權社會中。最重要的是,這不單單只是台灣父權社會的問題,而是全球父權社會至今仍擺脫不了的古老意識型態。這樣的迷思長期以來進行的是對女性身體的規訓與女性情慾的壓抑,而最後唯一能夠擁有主動權卻不受任何譴責的,還是男人,不管是台灣男人還是西方男人。
那些輕易相信了「台灣女人很好上」的人,似乎沒有進一步做以下實驗:試試看輸入其他國家。這時,你會驚訝地發現,當你打「中國女孩」,後面依舊會出現 「很好上」;當你輸入「韓國女孩」,搜尋結果也會有「很好上」;當你搜尋「美國女孩」時,還是會看見「很好上」……這一連串的實驗結果代表什麼?女人「隨便」與否,本身就是一個父權迷思。從來不會有人去討論一個男人「好不好上」或「隨不隨便」。「隨便」這個迷思,從來都只是用來拘束女人身體自由與自主情慾的父權社會意識型態工具。
於是,當你還生氣地跑去跟對方爭論,宣稱自己「沒有那麼隨便」時,你已經掉進了這個迷思的陷阱當中。我們應該做的,是推翻既有迷思,以及迷思背後所代表的整套父權社會規訓體系,而非走進陷阱中,試圖打一場你永遠也不會勝利的仗。
不管是與哪一國的男人交往,女人都不應該再受貞潔迷思與父權家/國規訓體系的限制。一個個離經叛道的俗世惡魔已經替女人樹立了典範。不管是家居空間的狂野性愛,公共空間的情慾展示,還是逃逸於家/國之外的身體自由,女人將化身一個又一個俗世惡魔,持續衝撞父權社會框架,永不道歉。
頁:
[1]